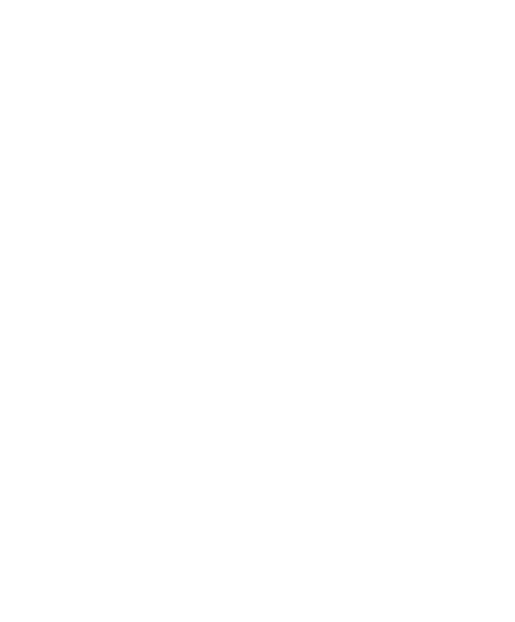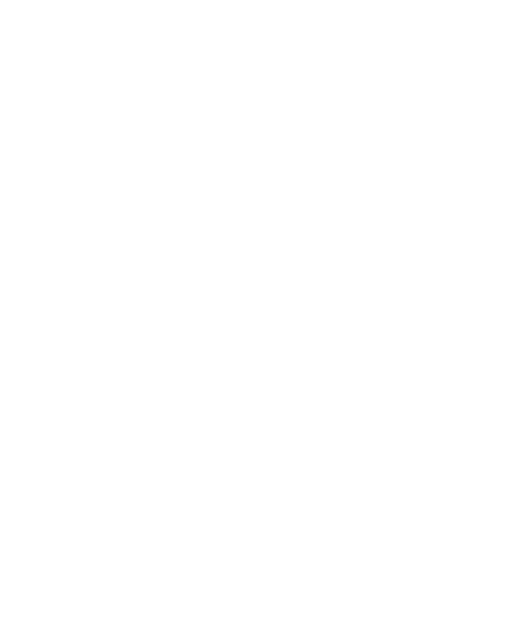桑植思源实验学校 黎伟
有人说“儿女生下来就是来向父母讨债的”。我和弟弟也许就是老爸身上最重、最难还的一笔债。
老爸又要转战新的“战场”了。十几年来,老爸的足迹到过靠近鸭绿江的吉林;去过比乌鲁木齐还远一百多里的新疆;也到过李冰治水的四川,还有拥有丰富煤矿的山西……前几年老爸更是漂洋过海的到了非洲——尼日利亚。当只有初中文化的老爸炫耀着他蹩脚的英语,将police说成“玻璃丝”时;当他非洲的同事得了急症不治而亡客死他乡,老爸却轻松地笑着说幸好提前回来了时;当我悄悄翻开老爸的记事本,看到用抽象的符号和中国字注释的英语时,我知道老爸身上背负了太多太多……
最初老爸的打工是被逼的。老爸开车做生意,车坏了,生意越做越差。老妈说路费是借的,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碗剩饭热给老爸吃后,老爸便离开了家,开始了他近二十年的打工生涯。
老爸第一次回家,是在离家之后的整整三年。我、老妈、弟弟一起去镇上接老爸。当老爸从车上下来时,我立马就认出了。我想大声喊老爸,可是喉咙好像被堵住了。我想跑上去,扑到老爸的怀里,可是挪不开腿。当妈妈拉着弟弟指着让他叫爸爸时,弟弟只是一脸的茫然,怯怯地往妈妈身后躲。当老爸给我和弟弟买了整整两排娃哈哈时,我和弟弟都笑了。老爸摸摸我们的头,轻轻说:“都长高了,长大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两排娃哈哈的味道。
家对于老爸来说仿佛是一座临时旅馆。只有过年时,老爸才会在这“旅馆”住上那么十几二十天,然后,背上行李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后来几年,老爸找工作不太顺利,便去了山西的煤矿。那时我们村上的人在煤矿里挖煤的很多。我已读高中,放月假回家时偶尔便能听到本村或邻村的人出事了。每当这时我只能默默地祈祷,或在极少数的和老爸的通话中羞涩地提一句保重身体。永远也忘不了老爸从煤洞回来时,我在车站见到他的第一面:老爸从到到脚都是灰黑的,黑色的外套如渗了油一般又油又黑;泥巴色的裤子变成了黑黄色;皮鞋上的煤灰好像已经变成了厚厚的保护层。老爸的头发像一丛枯草,胡子也是一个样,很久很久没有理了……“还没吃饭吧,走,吃饭去。”爸拎着行李领着我走进了一间小饭馆。我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老爸在外面吃饭。老爸似乎没有什么胃口,微微动了几筷子便停下来,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明显感觉到了老爸的目光,可是我不敢抬起头,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嘴里送饭,也不敢说话。我怕我嘶哑的声音和快要从眼眶迸出来的眼泪让老爸难堪。那次我吃完了满满一碗爆炒猪肝。觉得特好吃,特幸福。而老爸一个人从来是舍不得在外面下馆子的。
近几年,老爸就像一只风筝越飞越远,飘出了国界,越过了大海,到了非洲的尼日利亚。老爸只有初中文化,连普通话都说得不太标准。再加上老爸在赶去机场的路上还出了点小事故,所乘坐的出租车出了车祸,伤到了鼻子。因要赶飞机老爸没有处理伤口。到了尼日利亚,老爸也不知道怎么买药,整整流了一个多月的鼻血,鼻子才慢慢好起来。这些都是过了很久,老爸给妈妈打电话知道的。这一飘,老爸整整飘了十八个月。“那儿的人生活太差了,住的就是我们这苞谷杆子搭的棚子。还有好多人没有衣服穿,我回来的时候看他们可怜把很多衣服都送给他们了。那儿吃的也差,只产苞谷,一年可产三季,天天吃苞谷。我也就在他们那里买苞谷棒子吃。语言不通啊,要学啊。问人家,该学的学,该做手势的做手势……”这是老爸回来后和村里人聊天时说出来的。老爸还有一个本子,一个黑色的记事本。上面记录了他学习英语的方法,如汽车,他会先用笔画出一架小车,然后用汉字写出英语的发音。还有在一页上我看到了短短的一句话:妈妈我想你了!奶奶是老爸心中的痛——因在外打工,奶奶去世时他都没能赶回来。
老爸一刻都不给自己休息的机会。今年刚过完年, 他又开始漂泊了。这次他又要去越南……
“载不动,许多债。”老爸是一艘大船,我和弟弟便是这船上的载物。从我们读书开始,到供我和弟弟读完大学。这笔账让老爸由年轻变得沧桑,由强壮变得脆弱,由魁梧变得单薄。记得老爸曾半开玩笑地说:“还打两年工,打到五十岁了我就退休,回来好好过日子。”现在的老爸却依旧在山西,打电话依稀说了几次那边好冷,零下十多度。还是熬着没有回来。
老爸,回来吧!老爸,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