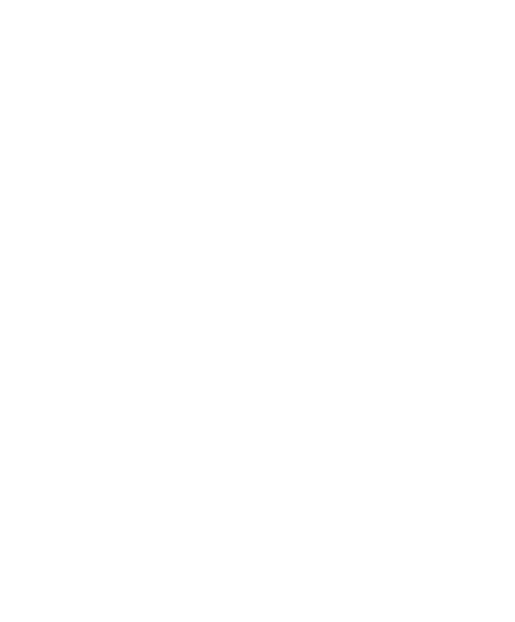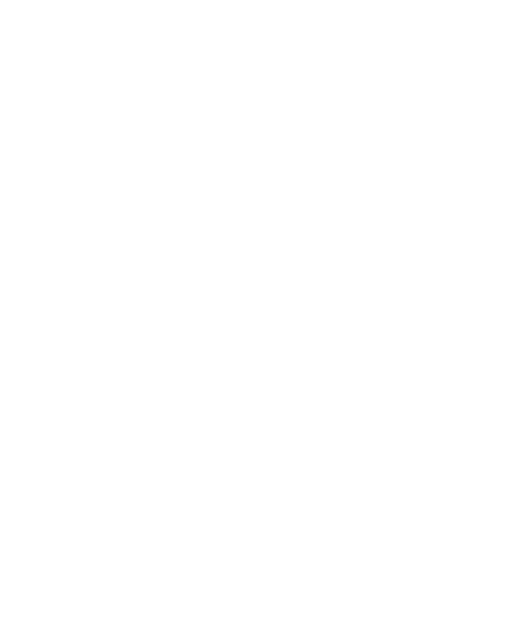□宋梅花
庸城,多么熟悉却又远去的名字。张家界的前身,叫大庸。说起大庸县,不能不说到南门口和十字街。这是小城内最繁华最热闹的地儿。数年如此,百年如此,直到,2016年,仅剩的南门口和河街几百来米长的老街全部拆迁。所有曾发生在这条老街的故事,都成为定格,成为人们永久的回忆。
作为从小在南门口长大的我,对南门口是何等的熟悉!于是,在我从2016年春天开始涉足学习写作小小说这种文体后,就在心里早早蕴酿着,要写出我的故事,写出我的周围父老乡亲们的故事,写出南门口、河街的故事。我自认为,我的人生,就非常具有故事。我那时想,我一定要写出我经历的人生,写出我的故事,这是我学写小小说时的初衷,加之从小爱好文学,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以后,我觉得,该是我排除一切困难,重新提起我心爱的那支笔。没有什么,再能挡住我那颗从小树立的文学之梦了。于是,2017年冬天,我的《庸城故事》100篇全部完稿,就像一位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摇摇晃晃却充满了顽强和执着,在我的小小说路上走来了!
顽强和执着,我想,这是庸城人特有的精神,我就是庸城人。《庸城故事》,以小小说文体为主,以讲述寻常老百姓的故事为主,文字朴素,内容朴素,然而却是洗尽铅华、接满地气。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在每一条青石板街,都能感觉有一股强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人物的嘻笑怒骂,个性场景的自然配衬,对南门口的回忆和对河街的留恋,都在这本书里能找寻到昔日庸城的影子。有读者说,我的庸城故事,充满了一种说不清的乡愁。还有读者说,我的庸城故事,充满了浓浓的怀旧。更有读者说,我的庸城故事,充满了款款深情。是的,都对。庸城的模样,我喜欢。说到十字街,就会想到原来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长得好高好粗。说到十字街,就会想到那座小石桥——东门桥。夏天,有在桥边卖西瓜卖桃子的,冬天,可以站在石头桥墩条边望着小桥下边很少很少的水。还有来来往往的背背篓的人,挑担子的人,空着手走路的人,老的,少的,他们从我面前走过,说话声音都很大。说到十字街,就会想到夏天的晚上那么一大群人围在街头,看着一个又瘦又矮眯缝着眼儿边敲打着腰上的鱼鼓筒边摇头晃脑的老人自我陶醉的模样,听着他那地道的庸城乡语的说唱声。说到南门口,便会想起航空技术学院那铁门里面平塔里开着的那丛星星点点的红色五星花,点缀在一大丛绿叶中,真是好看。所以,常常在傍晚,吃完晚饭便走出巷口,转悠到那座铁栏大门边,趁着守大门的老人不注意,侧身溜进去,等到他发现我进去时,我已满心欢喜地在五星花前看了个够。因为,那么大一丛红色的五星花,是那么充满了诱惑力地开在塔院里唯一的一小块儿竹篱笆小菜地边啊。说到南门口,便会想起南门大码头,在码头边滑着青石板下去,很好玩儿,但生怕滑进河里,待滑下去,却发现根本不会,因为那么多层的青石台阶下边,还有好宽的河塔,河塔边有成排的洗衣妇,河边停泊着成排的船。码头最上面那只断了耳朵和鼻子的小石狮子头上,早已被孩子们用手摸得滑亮滑亮了,每滑一次下去,都要以石狮子坐的那里为起点开始往下滑。说起南门口,还会想起几岁时婆婆牵着我的小手从北街上走到那个南门口最大的裁缝铺去铰扣子眼儿……总之,说到南门口,就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事儿,那时的南门口,热闹啊,是真的很热闹。在那时的很多人眼里,如从乡下上得街来,不从南门口走一趟,那不叫上街,因为那时,没有车,很多乡下人要上街,都得走路,近的,要走大半天才到街上,远的呢?有时一天都进不了城,待进得城来,那是理所当然地要去南门口的,怎么着也得买个什么,哪怕,买上几分钱的衣服扣子,买上几束棉线……
南门街的故事太多了,我的小小说就这样写下去了。我的庸城故事也就这样一直写下去了。
这次出版的小小说集《庸城故事》,是在我的小小说老师——著名文学评论家顾建新教授亲自指导下写成的,并作序且逐篇点评。部分篇目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具有地域特色,情节曲折,人物形象奇特。雅俗共赏,让读者读后定有收获。100篇小小说里,我挑选了96篇,小心翼翼地放进这本集子。集子共分为“人物篇”和“风情篇”,每一篇,会让读者在品读文中人物的嘻笑怒骂时,去领略庸城的风土人情,让读者在庸城的风土人情里,去欣赏各色人物描写。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的:“一草一木皆是缘,一字一句皆是情!我希望我们的庸城,更为美好!希望我们的张家界,以美好的姿态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更希望,我的这本小小说集,能像那在山野间自然开放的野蔷薇花儿,遇到风,就会香气扑鼻,读者,就是它的风,有了读者的喜爱,它便会清香四溢。小小说,就是我心中的野蔷薇花梦。我想,我会继续在小小说的路上努力的。我不敢苛求太多,只希望有一天,让人读到我的作品时,能感觉到有一股山野间野蔷薇花般的清香扑面而来,让人想到那山野间的一抹粉红,对于我,也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