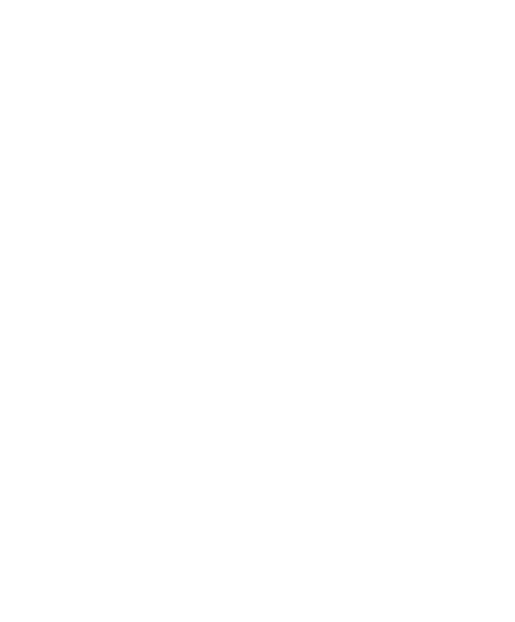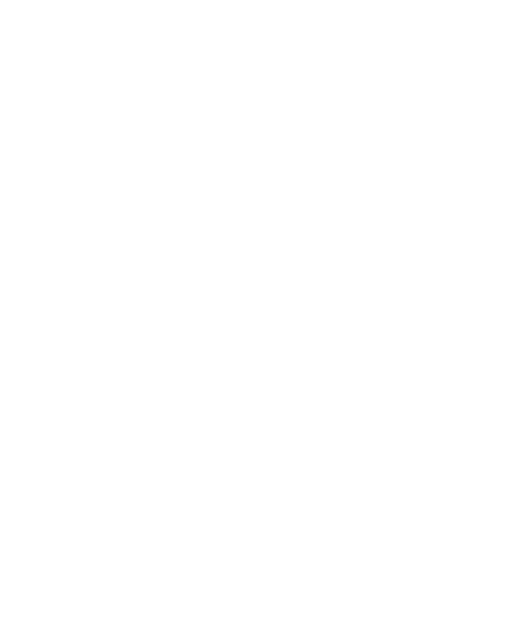覃正波
每年的霜降过后,各家各户就开始在火塘里生火了,做饭烤火两不误。柴烟在瓦房的空间里自在弥漫,乡下人终于可以不慌不忙地依偎在火塘边享受着幸福的日子。劳累了大半年的庄稼人,在这个季节串串亲友的家门,唠唠家常,谈谈儿女的婚嫁。主家们喜迎客家,把柴火添得旺旺的,屋内尽是温暖。
火塘,在我的家乡俗称“火坑”,用条石砌成,四周皆可坐人,一般设在宽大的堂屋里。空间大,可坐二十余人。乡下的火塘大气,和庄稼人豪爽的个性有关。
霜降过后直到来年农历二月,火塘里的火一直旺着。火塘最受欢迎的是树蔸。挖树蔸是个力气活儿,非力弱者所能为。大年三十夜,庄稼人最是要比谁家火塘里的树兜大。谁家最大,谁家最旺。于是,庄稼人农闲时便满山寻找老树蔸,燃烧的树蔸最好能延续到正月初二,把旺气带到来年。
火塘边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把蕃薯在火灰里烧,把土豆也埋在火灰里烧,极香,好吃得很。有的孩子把火灰弄得飞扬,自是召来大人的责怪:“这么玩闹,看我怎么收拾你!”大人板起脸,把手扬得老高,但落在孩子身子却是棉花一般轻柔。
火塘里最暖人的时日,当是腊月和正月。腊月,是杀猪宰羊打糍粑的月份。年肉一块块挂在炕上,不能断烟火,昼夜要有火气。庄稼人每天临睡前,都要往火塘里再加上几撮箕粗糠、瘪谷或者锯木粉,以便延续火星气。乡里人闻惯了柴火味,火塘里有烟火,梦里都是香甜的。
围着火塘,大人总喜欢讲些源远流长的传说。大人曾经给我们讲述后娘的故事:“前娘留鸡腿,后娘留鸡肠,想起来哭一场。”大人们把后娘讲得如此可怕,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对后娘充满了恐惧。一听到哪家离异或丧偶的男人娶了后娘,我们便替那户人家的孩子着急。后来,我们才发现,并不一定都是这样。
围着火塘,大人们讲忘恩负义的陈世美,说三国道水浒,谈古论今,用朴实的语言,道尽人世沧桑。留存在记忆深处火塘边的故事,始终温暖着内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普遍盖上了漂亮的新房,柴火燃烧的火塘渐渐地被电火、空调取代。但老一辈人闻惯了柴火味,总还喜欢在自己居住了差不多一辈子的瓦屋里生一塘柴火,任烟雾弥漫。
冬月底或腊月初,是屠夫生意最忙的时候,每天要奔好几个场子。年关杀猪是年味临近的前哨,腊月里,庄稼人会忙着杀年猪,将盐渍好的肉上架用柴火熏。庄稼人熏肉,一般都挂在火塘上方,烤火熏肉两不误。屠夫每天杀猪前都要拜神灵,请求上天宽恕开杀戒之罪。杀猪对于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来说无异于过节,但杀猪时,主妇们通常会蹲在一边,不忍看屠夫将尖刀朝自己喂养的猪刺去,怕猪望着自已掉眼泪。
打糍粑也是年关的要事,同杀年猪一样,是庄稼人必经的程序。无论家境多么窘迫,两百个左右的糍粑是要的,不能丢脸面,庄稼人早早地就准备了糯米、高梁、小米等粮食。
打糍粑前要准备大量的柴火。彻底清洗一年来布满灰尘的大石凳,把自家的两扇门板下了做压板。当然,棒槌、扁铲、桌子、竹垫也要弄干净,这些打糍粑所需物什都要涂上黄油,防止糯米沾着。待糯米蒸成八九分熟,便将糯米饭倒到石凳上。每每这时,孩子们便会打闹着伸出一双小手来哄抢香气扑鼻的糯米饭。有些害羞的孩子不敢,主人便用手捏一大坨送去。打糍粑的日子,孩子们吃了东家赶西家,小小的肚皮涨得滚圆滚圆的。打糍粑举棒槌的通常是虎背熊腰的后生,力下得重,饭锤得细,糍粑粘性足细腻可口。在寒冷的冬天,两后生光着肩膀,肌肉一块一块的强健有力,流着汗水,一锤,两锤……,边锤边喊:“迎新年,嗨哟!送旧年,嗨哟!”声如洪钟,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欢愉。待糯米团打成粑粑浆时,两后生用棒槌糯米团迅速挟起,放往抹了黄油的大桌子上,大家便争先扯着糯米团,开始做糍粑,捏成团,然后盖上门板,孩子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爬上盖板,或被大人们抱上门板,“咚咚咚”跳个不停。糍粑压得越薄越好,大人们认为孩子压力不够,还会叫有力气的男人抬上重条石压上。估计压得差不多的时候,搬下条石,孩子们喜滋滋地跳下门板,大人们用力掀开盖板,悉数取下糍粑放入箩筐。随着“再来下一锅!”大伙儿又开始新一轮的忙碌,只看谁家糍粑打得多,看谁家的糍粑做得更圆实。
家中有了糍粑才像过年的样子。
糍粑对于庄稼人来说,不仅仅为年关所备,也是庄稼人的后备粮。年后上山挖地整土整日忙碌,庄稼人会带上几个糍粑,中午时捡几根干树枝在田埂上生火,将糍粑放在火堆旁烤,烤熟的糍粑会膨胀得老高,到了极限便崩裂开来,吐出阵阵香气,吃在嘴里酥软肥美。如果带上野葱酸菜做馅,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我的家乡中湖,冬韵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