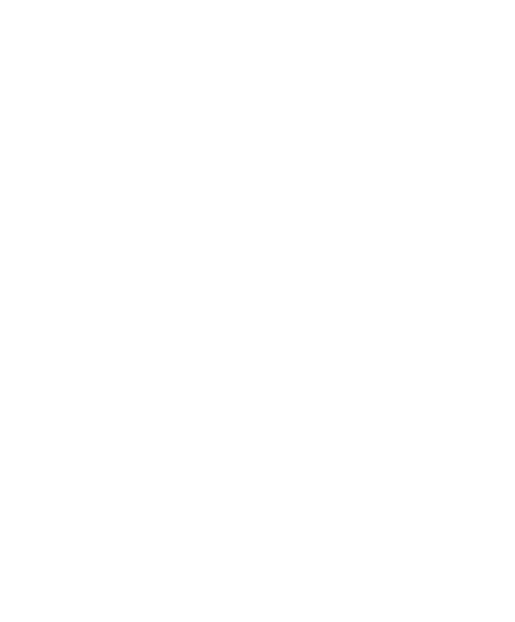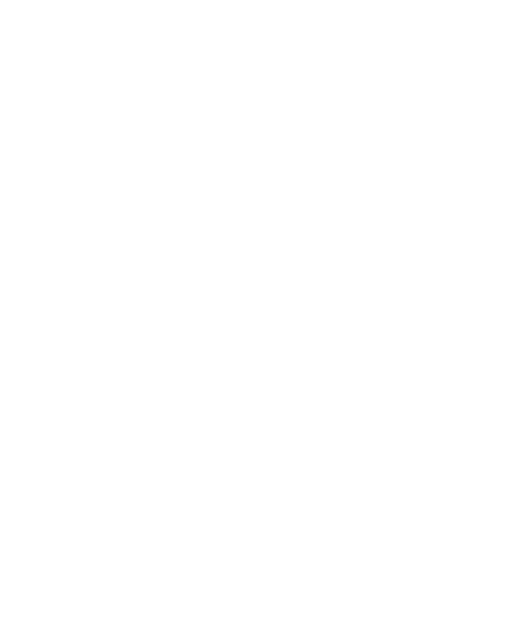王明亚
雪是天上一只大大的包袱,抖一抖,落些星星点点的碎末漫天飞扬。黄昏灰暗的天空里,闪闪烁烁,灿若萤火。仰面而望,珠珠粒粒跳降在唇眉之间,凉凉的,滑滑的,伸手去接,一颗,两颗,三颗,晶莹剔透,弹指消融,只留浅浅的一抹清凉衔在掌上,似一场魔术的表演。
这是天空蓄谋已久的雪事。它让乌黑的云低低地悬下来,让北风呼叫着东游西荡,让枝头残余的枯叶蝴蝶一样四处翻飞,让寒鸟慌张地稳扎窝居,让少有的温暖靠边站。它梳理出一条俯冲人间的大道时,我们已经做足了迎接一场雪的准备——棉衣加厚了,帽子戴上了,围巾绕上了脖子。来吧来吧,深冬的第一场雪!
风不想停下来,它躲在山与山的罅隙里,藏在屋与屋的夹缝间,隐在树与树的脊背后,不时沉着脸吹气,呼呼的,呜呜的,似吟似泣。天空飞洒的“萤火”越来越紧促,密密麻麻,窸窸窣窣,似宇宙星辰纷纷坠落。倏忽之间,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的雪花凌空飞降,飘飘转转,直让人眼花缭乱。
“飞雪带春风,徘徊乱绕空”。雪,如羽如棉如絮如千千万万撒欢的小仙女骁腾奋飞,一会儿顽皮地翻个跟头,一会儿翩翩起舞,一会儿长驱直下,一会儿盘旋跳跃,一会儿古怪精灵地谈笑着,嘻闹着,抢着步,比着赛,此起彼落中迷了双眼。渐渐地,大雪拉起一道朦胧的屏障,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了,只余了高低起伏的三两座,慢慢白了头。雪落在山脚的屋顶上,屋顶便泛出块块白斑;雪落在附近的菜畦里,菜青们便团团簇簇地穿起白纱裙;雪落在公路上,蜿蜒的公路便镶出两道白边;雪落在庭院里,光秃秃的树杆便有了素素的白艳,常青桂更增添出生命的厚度,庭前草缓缓地低头不语;雪落在身上,奔走的身子便有了雪花的舞姿……夜间,风稍停起来,逐步停了,世界在大雪的喧哗里静下来。
啾啾,一只小个子寒鸟惊惶地从窗前掠过,“吱”的一声,仿佛来自时光深处的另一些雪。
寒风袭卷后的傍晚,大雪赶集一样从天空来到大地,孩子们奔走相告,仿佛那雪只落在他家的院子里。然后静静地等待更大的雪,天明时好在田坡上弹跳,打滚,溜雪,烂漫的笑声回荡四野。——那是落在童年的雪。
裹着厚厚青花棉袄的妇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大喊:别把鞋踩湿了!别冻着了!别摔跟头了!——那是落在母亲青丝上的雪。
背着行囊“吱嘎吱嘎”走在雪地里,一步一回头地远去。——那是落在飘泊路上的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那是落在古人诗韵里的雪。
东风卷帘催梦醒,已是客居他乡人。——浅浅深深,那是落在一呼一吸里的雪……
雪,就这样轻轻悄悄不管不顾地下到天明。
我以为是天明了,时醒时梦之间,只见屋外天光泛白,推窗一看,呀,这还哪是昨天棱角分明的世界?——看不清远山如黛,看不清琼楼玉宇,看不清庭院里的枝枝树树,整个世界都被一只厚厚的白包袱包裹起来,炫目的雪光映亮了黎明前的黑夜。这是一个干净圣洁的世界,是一个静谧得听见心音律动的世界,是一个唯雪花说着它们古往今来的世界。
一开始呜呜咽咽的北风呢?
一开始颗颗粒粒的雪珠儿呢?
一开始千千万万的雪片儿呢?
一开始浸入骨髓的冷寒呢?
不见了,唯这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松松软软的一墨白,挥写出天地一线惊人的瑰丽。我想,那呜咽的北风送雪一程后已远归了;那颗粒的雪珠儿已成为积雪的基石;那万千的雪花已是大地银辉的影子;那嗖嗖的寒冷已被“咯吱咯吱”地踩在脚下。
雪,装扮了一树的琼花;雪,调和了一冬的颜色;雪,丰饶了大地的内容;雪,唤醒了贪睡的孩子;雪,激活了童趣的力量。庭院里,屋门前,街道上,人们惊喜地谈论着这场多年不见的大雪,孩子们快乐地滑溜出长长的雪痕,不时捏一个雪团,远远地扔出去,或三五个聚在一起滑雪、堆雪人,白茫茫亮灼灼的雪地里又多了几份生动。
恍惚间,我不知道这是故乡童年的雪,还是异乡今晨的雪;我不知道这是旧时落在母亲青丝上的雪,还是如今点染母亲白发的雪;我不知道这是我梦里啮咬贫寒的雪,还是现实里抒写暖意的雪。
我想到了封藏。雪是天空的包袱,它把一切脆弱的枯涩的弯曲的秃兀的污浊的严寒的都收藏起来,把美展现给人看。雪是一位美的艺术家。
我也想到了人生。时光也是生命的包袱,它把一切成长的困苦的磨难的疼痛的沧桑的都收藏起来,渡引人去看生命的欢愉。时光是一位宽容的人生导师。
一场风,一场寒;一场雪,一场美。人亦是,一场苦,一场甜;一场冷,一场暖。
感谢天空精心策划的这一场雪藏,感谢时光为我们收藏起过去鲜活的记忆。流光似水,生命归宁,抖开时光的包袱,曾经辛辣凛烈的灰暗有了亮色,点点滴滴的钝痛也长成了生命的骨髓。美好的事物虽然短暂,于全部的生命,也是刹那惊鸿的灵魂盛宴。